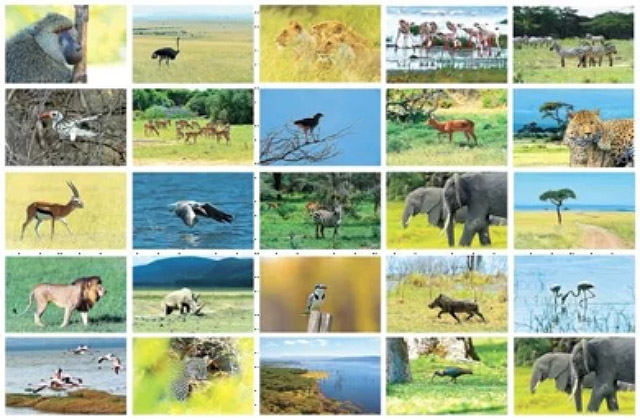中国的物种灭绝与绝处逢生
我国地大物博,生物多样性丰富,尤其是在人口迅速扩张或战乱的年代,不少物种悄悄地离我们远去。认识物种灭绝的历史可以让我们更深刻的领悟到做好保护的重要性及关键——合适的时机、有效的方法和多方的支持。从最初社会压根没有保护物种的概念,到逐渐累积知识和经验,终于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其中有一些失败与成功的案例,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现时生活在云南的非洲白犀牛
图片来源:普洱太阳河国家公园
中国的犀牛曾有三种之多——印度犀(Rhinoceros unicornis,又称大独角犀)、苏门答腊犀(Dicerorhinus sumatrensis,又称双角犀)和爪哇犀(Rhinoceros sondaicus,又称小独角犀),曾经广布于大半个中国。
在商朝(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相信北至内蒙古、太行山、泰山等地都有犀牛的踪迹。在唐朝(公元618-907年),犀牛分布已经缩减,但在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青海等依然有分布。到了明朝(1368-1644年),只有在贵州和云南还有犀牛的记载。到了清朝时期(1636-1912年),种群分布就只剩下云南了。专家认为,三种犀牛都曾经生活在云南,云南的西北部与藏东南和印度交界地区曾有印度犀,直到近代,云南的西部和南部有苏门答腊犀,而云南南部則有爪哇犀(何晓瑞 1994)。云南最后三头犀牛分别于1948-1949年在腾冲、1950年在勐海和1957年在江城被捕杀(许再富 2000)。神般的独角神兽从此在中国消失了。今天你在国内所看到的犀牛都是以后再引进的。

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年至公元9年)的铜制酒壶,身上镶有金银图案。1963年于陕西出土。
图片来源:BabelStone - Own work, CC BY-SA 3.0
犀牛角被视为一种珍贵药材,犀牛皮和血也可以入药,犀牛皮在古代更被用来制作士兵的皮甲。由于越发珍贵,犀牛角被制作成各种精美的工艺品,在国内外都曾是被追捧的稀世珍宝。在清朝,捕猎犀牛成了官府的特权,官员以犀牛角作为朝廷贡品。单单在二十世纪初,十年内就有300只以上的犀牛角被进贡到朝廷。除了人口扩张和过度捕杀,气候变化也是犀牛在我国绝迹的原因。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000年这个时期气候变冷,文献都有把圈养犀牛往南迁或冻死的记录。
在全球而言,印度犀从二十世纪初的两百多头增加至现时三千五百头以上,分布于印度及尼泊尔。苏门答腊犀只剩不到八十头,零碎分布于印尼的苏门答腊,而沙巴已知的最后一头犀牛也刚刚在11月23日去世了。爪哇犀就已经极度濒危了,只剩下在印尼爪哇的一个约50头的种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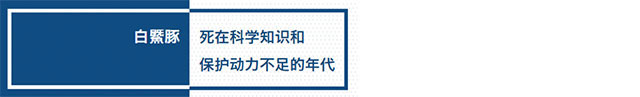

白鱀豚有长长的吻部和眯眯眼
白鱀豚(Lipotes vextilifer), 又称“长江女神”,是长江的特有物种,也是白鱀豚科现代唯一仅存的物种。曾经广布于长江流域,从三峡地区的宜昌葛洲坝一直到入海口,全长1700公里。种群数量估计曾经有五千头之多,1986年估计不及300头,到了1997年总数不足50头。
对于白鱀豚的研究始于1974年,但研究对象仅限于标本和尸体。1980年,一头年幼的雄性白鱀豚搁浅并被渔民送到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被取名“淇淇”。1981年,相继有另外三头白鱀豚被送到饲养单位,可惜都活不过一年。为了发展人工繁殖种群,给“淇淇”作伴,渔民捕豚队终于在1986年成功捕获一头成年雄豚“联联”和一头幼年雌豚“珍珍” 。同年举办了第一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就白鱀豚的保护提出三大措施: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人工繁殖。可惜,“联联”不到三个月就去世了,计划与“淇淇”配對的“珍珍”也在两年多后,在尚未性成熟的时候去世了。
为了保护白鱀豚,湖北石首天鹅洲国家级保护区于1992年成立,保护区除89公里的长江江段外,还有21公里的天鹅洲故道,该故道1972年以前曾是长江的一部分,后来通过开闸放水来维持与长江的连通(王丁,2000)。1995年捕获到的一头个体被放到这里,可惜1996年这头白鱀豚触网而亡。同年,捕豚队也曾经成功将三头白鱀豚围捕在渔网内,打算给铜陵白鱀豚养护场建立新人工种群,但起网时渔网竟然被礁石划破了,行动失败告终。
2002年,被饲养超过22年的“淇淇”自然死亡。虽然曾经有六头白鱀豚被人工饲养,但其实几乎所有现存的研究与影像数据都来自“淇淇”这单一个体。
最后一次在野外发现白鱀豚的确凿证据,是2004年在南京附近出现的一具尸体。2006年,国务院颁发了行动纲要,要对白鱀豚制定重点保护计划,然而为时已晚,60多名专家学者在长江进行了39天的考察,一头白鱀豚都没有发现。科考人员相信就算有少量的个体可能依然幸存,但野外种群应该已功能性灭绝。其后,还有一些考察及疑似目击,但都无法被拍到或求证。
白鱀豚的主要威胁来自长江流域的人类活动。20世纪采集到的白鱀豚尸体中,九成以上的死因是人为的。围湖造田减少了湖泊面积、水污染、噪音、渔船和捕鱼活动的直接伤害都对物种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如果白鱀豚被宣布野外灭绝,这将是50年来第一种大型脊椎动物的灭绝,也是第一种由于人类活动而导致灭绝的豚类动物。
那为什么40年的研究与保护都无法挽救白鱀豚的种群?根据《Witness to Extinction – How we failed to save the Yangtze River Dolphin》的作者分析,我们错过了最后救援白鱀豚的时机,因为当时(1)缺乏对该物种的认识(几乎所有数据均来自“淇淇”一个个体,而这个物种又与其它物种差距甚远),使人未能制定一个完善的迁地保护和人工繁殖计划,(2)一些人悲观地认为白鱀豚无法在人工饲养环境下繁殖(根本没有依据),妨碍了所需经费的筹募,(3)一些人认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整体恢复与保护是唯一挽救白鱀豚的方法,而忽略了迁地保护工作必须同时进行的迫切性。
在危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用非常手段,但谁担得起这种责任?谁冒得起这种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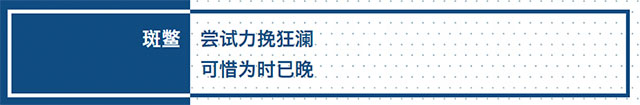

图片来源:Tim McCormack
斑鳖(Rafetus swinhoei)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淡水鳖,背甲长度可达1.5米,体重可达115公斤以上,曾经广布于我国长江和红河流域,以及越南的北部地区。云南境内的斑鳖到60年代还有不少,而中国最后一只野生斑鳖于1998年在红河被发现,之后被野放了。由于分类的不确定性,该物种长期被忽视,在90年代以后该物种才逐渐被认识和被关注。
苏州西园寺内原来有一雄一雌,据称它们在清末(1830-1890年)被放生于此,但雄性斑鳖“方方”于2007年以400岁高龄自然死亡,雌性“圆圆”后来也一直不见其芳踪了。

原来在越南河内市内12公顷的环剑湖内有一只,但在2016年去世。
图片来源:Rick Hudson
2007年,长沙动物园一只80岁的鳖被认定为雌性斑鳖(在鳖的世界还算年轻),经历了两年的谈判,2008年长沙动物园终于同意把斑鳖送往苏州,本园也是计划支持单位之一。经历了一千一百公里的长途跋涉后终于抵达苏州动物园与命中注定的百岁爱郎相遇。据专家介绍,这两头斑鳖如果饲养得当,应该还能多活两三百年。2009年两小口已经发生了交配行为,并产生四窝卵,当中包括为数不多的受精卵。很可惜,无论在原地还是送到孵化箱的卵都在一周内停止发育了。经过6年的努力都未能成功自然繁育,期间产下的数百个卵都无一能成功孵化。2015年的生殖评估显示,雄性斑鳖生殖器受损,精液质量较差,继而马上启动了斑鳖的人工受精工作。自2015年来四次的人工受精均未成功。在2019年4月实行的第五次人工受精过程中,雌性斑鳖不幸去世了,这意味着这个物种可能已“功能性灭绝”。经过科研人员多年的努力,还是无法帮助最后的斑鳖开枝散叶。
在2014-2018年间,曾收到过在红河流域疑似斑鳖的目击报告,但都未能核实。无论是在我国还是越南,物种的威胁主要是栖息地丧失,水质污染,繁殖场所(河岸沙土)孵化条件不稳定(由于水坝工程等水位变化太大),人类干扰和捕猎(食用及作为宠物)。
现在,人类已知的斑鳖个体还剩3个,我国最后一只雄性个体身处苏州动物园,另2个性别不详的个体在越南野外,分别是东莫湖(Dong Mo Lake)和宣汉湖(Xuan Khanh Lake)。宣汉湖的个体是在2018年通过环境DNA手段确认的,因此也没有人见过其庐山真面目。
看来,要成功恢复种群比较渺茫了。


麋鹿真像是长有鹿角的牛,摄于江苏大丰麋鹿苑
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是自古闻名的“四不像”;它有马的脸,鹿的角(其它的鹿角是往前方生长的,但麋鹿的角是往后的!),牛的蹄子和驴的尾巴。麋鹿原来广布于我国长江中下游的沼泽地区,西至山西省的汾河流域,北至辽宁省的康平,南到浙江省余姚,东至日本和台湾都有分布(张林源等 1998)。由于大量猎杀和湿地被大面积改造成农田,其数量在商周以后(公元前256年)迅速减少,在明清时期(1368年后)已几乎在野外灭绝,只有泰州、海安、南通等地有少量的分布(张林源等 1998)。
不幸中之大幸,就是因为它备受狩猎者的喜爱,在元朝期间(1271年—1368年),蒙古士兵把一些麋鹿运到北方的狩猎场内供皇子皇孙游猎,因而到了19世纪,北京的南苑皇家猎苑保存着全国最后的200-300头麋鹿。可惜到了1900年,南苑皇家猎苑被八国联军占领,那里仅剩的20-30头麋鹿也在这个时候覆亡了。

雌性是没有角的
1865年,法国传教士大卫神父(Pére Armand David)窥探南苑时意外发现了未被西方社会所认识的麋鹿,成功取得一些骨骼和皮张送往法国进行分类鉴定,并以他命名。直到神父1874年离开中国以前,在他的协调下,有一些麋鹿被送往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地的动物园作为展品。在1894-1903年间,英国贝德福德公爵十一世把18头散落在欧洲各处的麋鹿买下,放养在他的私人府邸——乌邦寺庄园内,建立并保存了后来全球唯一的繁殖种群,在1945年的时候种群已发展到250头。为了安全度过二战,乌邦寺庄园向世界各地的动物园输出麋鹿,使得麋鹿这个种群得以保存。

湿地是麋鹿的自然生境,在江苏大丰麋鹿苑的部分麋鹿会在经过一定时间的半野放生活后才被放归野外
1985年,贝德福德公爵十四世向中国赠送了22头麋鹿,促成我国的麋鹿历史性地被重新引入放养于南苑皇家猎苑的旧址——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内。为了加快该种群的复壮速度,1987年又从乌邦寺庄园迁来另外18头。为了野放日益壮大的种群,94头麋鹿在1993-2000年间被送往湖北省石首市天鹅洲自然保护区。另外在1986年,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从英国伦敦动物学会下属7家动物园引入麋鹿39头,并于1998年开始在原址进行野放。这些海归麋鹿经过三十多年的悉心保护,现在种群已发展到6000头以上,成为一个经典的保护案例。


图片来源:国家林业局
朱鹮(Nipponia nippon)是一种中型的涉禽,身长80公分左右。它有很特殊的构造,会在繁殖期从头至肩的皮膚分泌出黑色的粉末状物质,令羽毛颜色变灰。朱鹮在日本被视为圣鸟,其羽毛会在一些皇室仪式中被供奉。它的闻名还在于,全球现存的三千多只(我国约两千六百只,其余在日本和韩国)均源于我国的七只个体。曾经把朱鹮推到灭绝的边缘的,一是当时广泛使用的农药DDT影响了其繁殖率,二是朱鹮喜欢在农田间觅食因而容易被捕猎,三是河流污染导致其食物减少,四是可供营巢的林木日益减少。
朱鹮曾经广泛分布于我国东北、台湾,日本、朝鲜半岛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等地。数量之多曾经被日本农民视为“害鸟”而作驱赶。在我国陕西和甘肃,20世纪初都还有大量的朱鹮繁殖记录。但自此以后,朱鹮的数量急剧下降,俄罗斯最后一次的记录在1963年,中国最后一次的记录是1964年,朝鲜半岛的最后一次记录是1979年。多年来专家努力寻找还是一无所获,曾经被认为已灭绝。
兴幸在1981年,日本科学家在野外发现了5只朱鹮,同年,中国科学家也在陕西发现了7只,并立刻成立了保护小组进行就地保护, 1986年陕西省朱鹮保护观察站成立,2001年陕西朱鹮自然保护区成立。另外,于1981-1988年先后被送往北京动物园的6只朱鹮在1989年人工繁殖成功。到2015年已发展到19个人工饲养种群,数量达1100只(国内800只,日本及韩国300只),而现时国内已野放的朱鹮有200多只。
虽然日本在1981年就开始了人工繁育,可惜以失败告终。1998年,中国政府向日本赠送两只朱鹮“友友”和“洋洋”,2000年再赠送“美美”为“友友”和“洋洋”的儿子作伴,2007年再有“华阳”和“溢水”抵达日本。至今,重新引入日本的种群已发展到400多只,而被野放的朱鹮已达200多只了。
2008年及2013年,中国政府分别赠送了一对朱鹮给韩国,并传授饲养技术。人工饲养种群到今年已发展到363只,并已在今年完成了首批40只朱鹮的野放。

不要忘了,还有我们一直关注与保护的海南长臂猿和海南坡鹿,它们的种群数量也曾经跌至十多头和四十多头,在这里就不再复述。
了解到这几种动物的保护历程,大家有什么感触或领悟呢?
这些案例说明,我们不应为动物保护订下“死线”。就算是到最后“一兵一卒”,只要有专业的团队用科学的方法,有相关部门提供政策和财政上的支持,加上社会的关注和配合,停止对物种的一切人为伤害,“绝处逢生”并不是不可能!